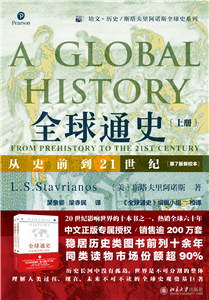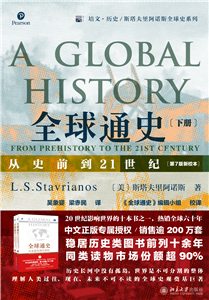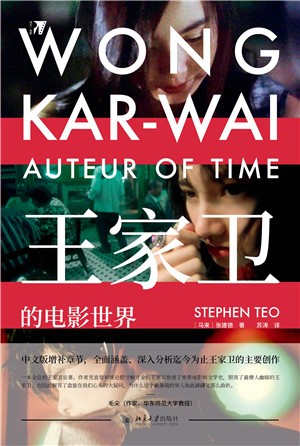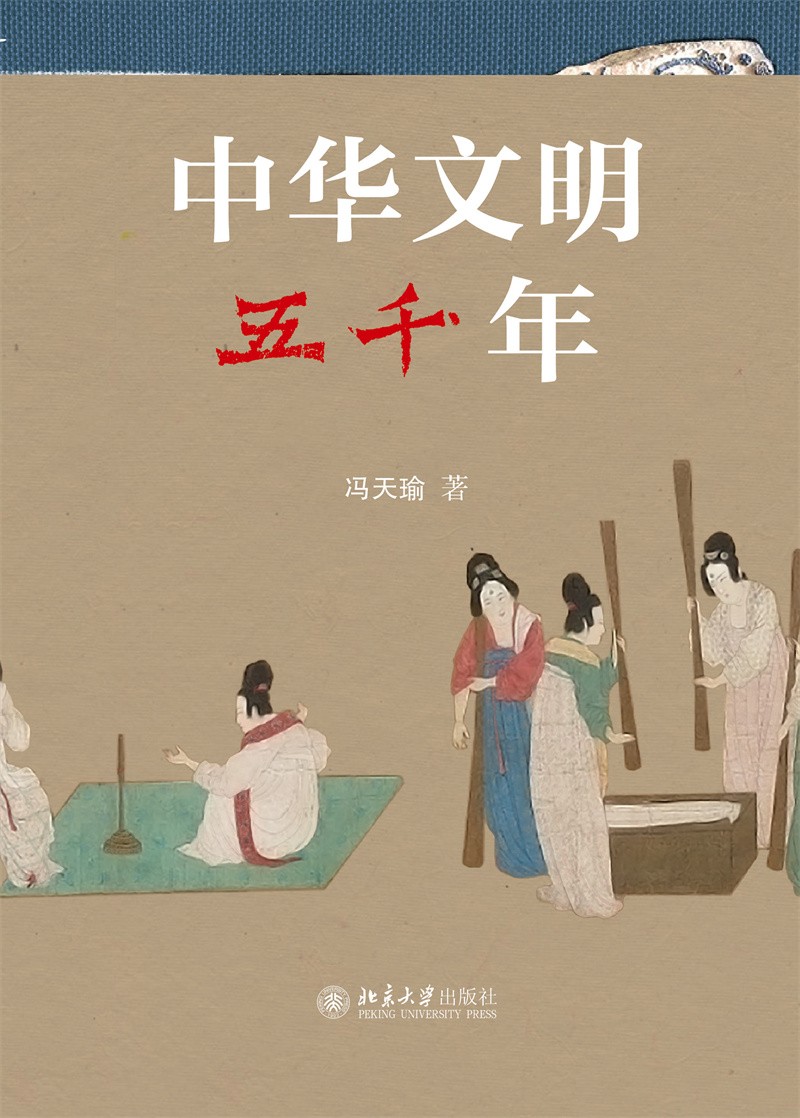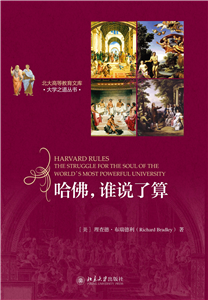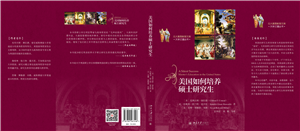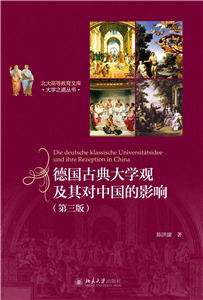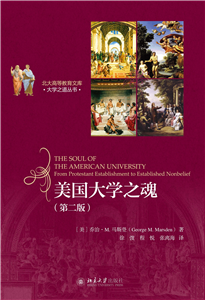·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
·目 录·
前言: 新的大学 / 1
第一编 高等教育的市场
一 这个幼小的学生去了市场 /
身份盗窃 /
马加尔的方式 /
吸引学生的诱饵 /
产品标价 /
不惜代价:改变学院经历 /
操纵市场 /
“我指导的不是申请,是生活” /
有可能进行“地区军备控制”吗? /
二 尼采的地位:芝加哥大学 /
罗伯特·赫钦斯的幽灵 /
问题的核心 /
但丁还是德里达? /
与雨果的矛盾 /
数字 /
雨果之后:更加平静、温和,并且几乎没有变化 /
三 本杰明·拉什的“孩子”:迪金森学院
/
濒临灭绝的种类 /
“没有因英语而死” /
形成“思想共享” /
学院大门上的牌子 /
四 星球大战:纽约大学 /
被马卡罗尼公司拯救 /
很多的意见,很多的机会 /
分析哲学是最优秀的 /
分析哲学的知识领域 /
纽约大学的“第二哲学系” /
一个共产主义版本的全球性大学? /
第二编 管 理 原 则
五 过去的阴影:纽约法学院
/
先例的阴影 /
现实的影响:芝加哥—肯特 /
“劲量兔子”:佛罗里达大学 /
“如果你能在那里做到……”:纽约法学院 /
六 卡夫卡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南加州大学和密歇根大学 /
外包:从餐厅到学校的“商标” /
“人须自立” /
USC:特洛伊战争 /
密歇根大学:“地方支持”的限制 /
七 杰斐逊先生的“私人”学院: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 /
自治的漫长道路 /
“特许费用”的谈判 /
达顿校区的“旅馆” /
托马斯·杰斐逊的巨型大学 /
市场与圣父 /
第三编 虚拟的世界
八 反叛联盟:南方联合大学的古典学系 /
“为我们的产品创造需求” /
古典学的复兴 /
古典学家的先锋 /
眼前的问题 /
教授们的推动 /
今天的校园,明天的哈佛 /
九 概念中的市场: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
“天生权利”的市场化:哥伦比亚大学 /
“知识共享”:麻省理工学院 /
网上大学的教训 /
十 英国人来了——又走了:开放大学
/
“无产阶级的学院” /
推广到国外 /
质量不是一切 /
金钱和“有意义的革命” /
第四编 机智地赚钱
十一 广泛协作:伯克利加州大学 /
大学出租? /
拼凑 /
进入伯克利 /
保持开放 /
与魔鬼共舞 /
吉规模Ⅱ,吉规模Ⅲ /
十二 技术信息淘金热:硅谷的IT证书课程 /
人人都可以参加 /
希尔德学院与优尼泰克:了解顾客 /
精明的消费者 /
加维兰社区学院:普及IT培训 /
圣荷西州立大学:竞争赢利 /
圣克鲁兹加州大学:优越感的矛盾心理 /
学术价值有市场吗? /
十三 他们都在经商:迪弗莱大学 /
“迪弗莱大学:直上云霄” /
但这是高等教育吗? /
结语:学习公司 /
回到未来 /
个人财产和公共利益 /
致谢 /
中英译名对照表 /
前言: 新的大学
大学是一个共同体,学者和学生在这里寻求真理。
——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的理念》(1946)
知识是一种风险资本。
——米歇尔•克罗,《高等教育周刊》(2000)
这两个校园之间只有半小时的车程,但在心理上的距离却有一光年之遥。在它们之间,标志的是美国新高等教育的外在差别。
第一个校园是现代版本的常春藤学院,一个与平淡乏味的世界相隔离的学习场所。这是一个真正的公园,青葱翠绿,掩映在周遭的公园之中,里面有池塘和蜿蜒的小径,是一个吸引学生和教师们来此进行对话的地方。这里的建筑现代而不张扬,大部分教室的大小只适合上讨论课,而且配备了电子时代的设备。这是一所选拔严格的学校,它的学生和工作人员来自全球各地。对于在这里所受到的教育以及接触相关事业的机会,学生们感到非常满意。
另一个校园是城市丛林中的一座仿哥特式建筑——那是犹太人区的“牛剑” 。但迄今为止,那些暴露出的疏忽的痕迹仍然随处可见,从20世纪50年代最先进的物理实验室到用于奥运——1908年奥运会——选手训练的游泳池。从建校到现在,学校始终陷于经济困境之中。前些年,它有两次几乎难以为继,预计中的每年一千万美元的赤字吞没了杯水车薪的捐赠基金。就连那些非常忠实的毕业生中也有很多人认为那里过于残酷,不会再将自己的子女送去读书。吸引新的生源变得越来越困难。2000年,申请入学的学生中有60%被录取,但最终来注册的却不到其中的三分之一。
这第二所学校就是芝加哥大学。第一所却是汉堡包大学——麦当劳公司培训总部。
将麦当劳与芝加哥大学相提并论可以说是一种亵渎,至少在海德公园里是如此。但汉堡包大学这类学校的声望日隆——当然,并非你父亲所接受的高等教育,而是一种经过认证的、正规的学校——以及芝加哥大学这类高级学术院校所面临的艰难选择说明了一个更加广泛的现象。无论是福是祸——抑或福祸双至——市场的力量和道德标准都改变了美国的高等教育。下面的章节中要叙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为了控制复杂的市场而采取的策略,以及这些策略给大学生活的价值所带来的风险。
高等教育是一个“市场”,这一观念还需要加以解释和说明,因为这一体系看起来与任何一本经济学概论教材所描述的市场都没有相似之处。在商业领域中,当市场供不应求时,公司便应该扩大规模,否则便会抬高商品的价格,这是一种鼓励新参与者的现象。但高等教育的运行却完全不是如此。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进行中学后教育的学校的注册率上升了一半以上,但增长的大部分来自社区学院——它们吸收超过30%的本科生——和地方性的公立大学。扩大这一概念本身是为精英分子所不齿的——想象一下在旧金山湾区开一家耶鲁分店。相反,这些学校把录取的标准定得前所未有的高。选拔最严格的学校会拒绝八个申请者中的七个,而其实几乎所有的申请者都是合格的。
大学并未提高价格来使申请就读的学生望而却步。尽管学费在不断上涨,尽管各个大学都在进行经济学家所称的“阵地战”以保护自己在排名中的地位,但学费上的收入仍然无法使其实现收支平衡。要确定一所不给学生资助的非营利性学校是很困难的,在强弱次序中的位次越高,给予的资助就越多。居于顶尖地位的学校用慷慨资助来吸引优秀的研究生。
新的学校意识到了在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环境中挣钱的可能性,也开始进入这一领域。但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学校并不能体现传统市场中的严酷的利己主义。它们用联邦和州贷款计划的方式接受大量的资助,这项行动比一家新运输公司或者芯片生产商最疯狂的梦想还要疯狂。由于营利性学校的所有学生都依靠贷款来支付他们上学的费用,那么如果没有得到初创新兴产业的政策,这些学校便不得不进行紧缩。
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这一特殊市场的“销售者”——即大学——寻求的是最出色的“购买者”,即学生。宝马公司并不在意是谁买走了它的车,但“在大学的生产过程中,消费者是最重要的投入,这与提供传统的私人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商不同……(精英学校)需要拔尖的学生,就像拔尖的学生需要它们一样”。如果对高等教育市场最恰当的理解是将它视为一种比喻而不是一种精确的经济模式,那么这种比喻便具有强烈的效果。
尽管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美国的大学一直期望能够成为学者和自由思想的园地。长达一个世纪的学术自由运动代表了一种不惜代价的努力,以确保与日常的压力保持一种心智上的距离,让学者们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来批评当时传统的知识。
重要的是不要将学术界传奇化,不要对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时代怀有思念之情。美元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车轮的润滑剂——如果事实是相反的话,“遗产”二字对于大学便没有了明确的意义。现实不会回到19世纪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的理念》中去,该书认为“有用的知识”是“一堆垃圾”,也不会回归到八十多年以前索尔斯坦•凡勃伦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所设想的那个世界,在那里,纯粹的研究是大学唯一的恰当行为,而推进有用的实用知识(和教育本科生)是较小、较普通的大学的任务。自从三个多世纪之前哈佛大学和威廉与玛丽大学敞开它们的校门以来,钱一直是一个紧迫的问题,而至少从发起大学赠地运动
的1862年莫里尔法案以来,有用和可用的教育的必要性一直是美国公共政策的主题。
真正新的、给人们带来困扰的是钱的原始力量对于高等教育很多方面的作用。即使是当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诸如平权运动和转换这样的原则问题上时(比如说像荒唐可笑的原则战争),美国的大学也在忙于彻底改造以适应激烈竞争的压力。学术界曾认为企业家的野心必然是邪恶的,而它现在却成了一种美德。“我们是在经商,”康涅狄格大学的教务长坦率地说,“我们的股东是学生、职工和康涅狄格州。”甚至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长也声称“加利福尼亚大学意味着经商”。
高等教育中的优先权更多地是由多种支持者——学生、捐助人、合作者、政客——来决定的,而不是学校本身,这些支持者中的每个人都在推动他们自己所理解的“有反应的”(事实上是服从的)学校。强有力的领导层曾被认为是创办一流大学的关键,而现在,那些校长们都在没完没了地忙于筹集资金。消费者、资金保管者、适当的市场、创造品牌、胜者通吃这些新名词代表了高等教育“产业”中的这一变化。这不是语义和符号的问题,因为商业词汇会加强商业化的思维方式。每一个系科都是一个“收入中心”,每一位教授都是一个企业家,每一个单元都是一个“资金保管者”,每一所学校都在追求利润,无论是以金钱资本的方式抑或智力资本的方式。
选择逃离市场来退出角逐是不切实际的。梭罗认为,从事教育便是处于一个捕鼠器之中,质量是最重要的,而任何一所采纳这种观点的学校都会导致自我毁灭。甚至——也许尤其是——精英学校也永远是保持警觉的,生怕被对手窃取了一点优势(或者是一位教授、一个主要捐赠人)。在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和文理学院中,声望就是金线,而由于声望是稀有商品,因此失败者要远远多于获胜者。
声望不只是意味着吹嘘董事和毕业生的权利,它会带来切实的利益,名声上的细小差别会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学校的声望越高,就越能吸引拔尖的学生和著名的教授,也更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资助(因为资助人相信能带来金钱的是金钱,而不是需要),来自政府和基金会的最大型的研究资助,常常还能获得最能盈利的行业合同。这样的成功可以稳固一所学校在强弱顺序中的地位。正如《马太福音》中的教义一样,“已经拥有的人应该被给予得更多”——也就是说,越多就越多。“在一个也许只有流行夜总会竞争的市场中,”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在描述他所说的“胜者通吃”的市场时写道,“高等教育是一个‘成功带来成功,失败带来失败’的产业。”
不论是否涉及本科生、教员、捐助者或者商业行为,近年来这一竞争已经变得更加激烈。优秀的学生对自己的选择更加有见识,因为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这样的出版物每年对“美国明星大学”的调查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也有更大的灵活性,另外,对于上榜的学校,他们也要求提供更加豪华的宿舍和更多的学费“折扣”。最受欢迎的学科认为自己首先附着的不是学校也不是本专业,而是他们自己。对于那些少数的幸运者而言,每年春天都是一个贪婪的季节,因为聘书的竞争力不仅仅取决于薪水,而且还有研究基金、教学工作量的减少等等。
随着大科学的来临,研究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学校聘请一位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可能要花费25万美元,但如果请一位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再配以助手和实验室,可能要花2000万美元。抓住这样一个人物不仅是一种投资,也是非常聪明的举措,因为在这些实验室产生的研究结果有着巨大的商业潜力——最成功的大学可以获得9位数的收入,这相当于获得了几十亿美元的捐赠。因此提高研究基金、争取专利权、在互联网上争取一席之地等行为变得越来越激烈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高等教育在顶层等级分明,但它还是越来越普及了。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比例在上升,还有越来越多已经工作的成年人回到校园。在学术阶梯的低处,重要的是金钱和注册数字,而不是声望。选拔条件相对较低和不进行选拔的学校——每五个美国大学生中有四人进入的是这样的学校——则努力让自己的教室坐满,它们依靠的是Priceline.com之类的打折和冷不防给人打电话的中介公司的帮助。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生的兴趣明显地从文理学科(liberal arts)转向了所谓的“应用型文理学科”(practical arts),因此大多数学校也随之调整了它们的课程设置。新一代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学校把这一部分的目标对准了市场。这些学校中的最优秀者与旧式的“火柴纸板”式的中等专业学校毫无相似之处,它们一方面将2%的学生吸收到自己的学校,一方面挑选了最有利可图的领域。没有人争抢哲学专业的学生。凤凰城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在争夺商科学生,迪弗莱大学和北伊利诺伊大学在抢招软件工程师。而且,营利性学校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不牺牲质量的情况下克隆自己,那是公立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不会做也不愿做的事情,而且他们还在潜在的互联网市场中取得了优势。
似乎对传统高校的这种挑战还不够激烈,还有超过100万的学生(其中有很多人原本会进入四年制的大学)选择了为就业做准备的信息技术课程这一“类似中学毕业的体系”,如思科或微软证书工程师。不仅仅是营利性大学和社区大学在追逐这些学生,择优录取的学校也将胳膊伸进了这个游戏。在这里,和远程教育一样,精英、大众和综合性学校之间常见的区别变得模糊了,声望和质量都不能确保在这一领域内的成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的重演。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前,芝加哥大学用高薪挖走了克拉克大学最好的教授;南加州大学开办了房地产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开办了一个像工厂一样的通信学院;还有麻省理工学院,普通电子系在学校建立了合作赞助的实验室。
关键性的不同在于这些力量的大小。大卫•里斯曼和克里斯多佛•詹克斯在1968年的著作中,将从奇普斯先生的“二战”前平静的学术村庄到克拉克•克尔的综合性“巨型大学”的转变过程称为“革命”,而“革命”至少是对当前克尔本人所说的高等教育的“最重要的时代”的一个极好的描述。新的教育技术,有着不同期望的学生和有着不同要求的教员,在市场中活着或死去的不同竞争对手,不断要求新的基金和新的收入来源以代替越来越少的公共资助,头脑中真正的传统大学和营利性大学的精神斗争,优秀系科的协作和信息技术证书课程的竞争,挑选学生和网罗著名教授。
这些陈述有没有体现看不见的手的良性动作、西方的衰落或者——相似或者不相似的——即将到来的事物呢?有些陈述描述了已经知道如何将学术和市场这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的学校,它们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市场中成功而有原则的竞争者。其他的陈述则是关于那些达成了只有浮士德才会喜欢的契约的学校。哪一种模式会主宰高等教育的前景?这是一个赌注。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当答案出现的时候,它会描绘出高等教育未来的方向。
本书描述了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因持续加速的市场化而造成的巨变:为竞争精英学生,各大学将自己“品牌化”以增加吸引力;对学术超级明星开出天价工资以提高大学的知名度和声望;由纳税人资助的学术研究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专利;学术思想以最高的价格被竞价者买走;在市场经营的压力下,文科逐渐萎缩。
本书指出,市场在高等教育中应该有一席之地,但同时又必须恪守界限,不能超越高等教育的底线。
大卫•科伯(David Kirp),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公共政策教授,著述甚丰。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学。
如何将大学院系变为获利中心?如何防止产业对科研进程横加干涉?学术活动遭遇利润盈亏问题时会怎样?本书对这些重大的问题进行了精彩的剖析和探讨。
本书描述了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因持续加速的市场化而造成的巨变:为竞争精英学生,各大学将自己“品牌化”以增加吸引力;对学术超级明星开出天价工资以提高大学的知名度和声望;由纳税人资助的学术研究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专利;学术思想以最高的价格被竞价者买走;在市场经营的压力下,文科逐渐萎缩。
本书详尽探讨了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内强劲的市场化动力,既赞赏企业化的活力打破了学术界的沉闷氛围,又对商业价值和市场标准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泛滥怀有隐忧。本书指出,市场在高等教育中应该有一席之地,但同时又必须恪守界限,不能超越高等教育的底线。
本书案例典型,眼光独到,叙述生动,结论极富于洞察力和启发性,是高等教育及公共政策等相关研究领域研究者的必读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