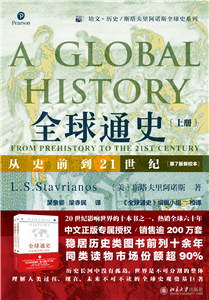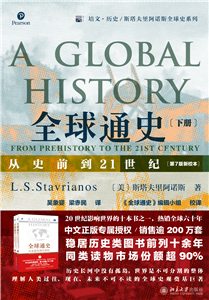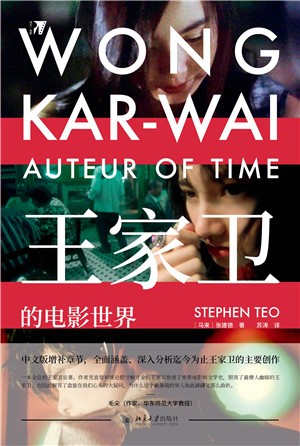首页图书
基本信息 Information

梵汉本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词语研究
目 録
序 言 王邦維
前 言
第一章 中古佛教律典的梵漢語料概觀
第一節 中古律典的梵漢文本概述
第二節 中古漢譯律典詞語研究的語料來源
第三節 中古律典詞語的研究趨勢與方法
第二章 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的翻譯及其流傳
第一節 “遍翻三藏、偏功律部”:義浄的翻譯事業
第二節 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漢譯本的敦煌與西域寫卷及其比勘
餘 論
第三章 梵漢本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的名物詞選釋
第一節 音譯名物詞選釋
第二節 意譯名物詞選釋
第四章 梵漢本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的疑難詞選釋
第一節 音譯疑難詞選釋
第二節 意譯疑難詞選釋
第五章 梵漢本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的常用詞選釋
第一節 有梵本對應的常用詞選釋
第二節 無梵本對應的常用詞選釋
第六章 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譯本的句法處理
第一節 漢譯本對梵本的句式轉换或句型改譯
第二節 漢譯時不改變句型而對句子内部的成分加以調整
結 語
主要參考文獻
詞語索引
致 謝
序 言 王邦維
前 言
第一章 中古佛教律典的梵漢語料概觀
第一節 中古律典的梵漢文本概述
第二節 中古漢譯律典詞語研究的語料來源
第三節 中古律典詞語的研究趨勢與方法
第二章 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的翻譯及其流傳
第一節 “遍翻三藏、偏功律部”:義浄的翻譯事業
第二節 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漢譯本的敦煌與西域寫卷及其比勘
餘 論
第三章 梵漢本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的名物詞選釋
第一節 音譯名物詞選釋
第二節 意譯名物詞選釋
第四章 梵漢本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的疑難詞選釋
第一節 音譯疑難詞選釋
第二節 意譯疑難詞選釋
第五章 梵漢本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的常用詞選釋
第一節 有梵本對應的常用詞選釋
第二節 無梵本對應的常用詞選釋
第六章 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譯本的句法處理
第一節 漢譯本對梵本的句式轉换或句型改譯
第二節 漢譯時不改變句型而對句子内部的成分加以調整
結 語
主要參考文獻
詞語索引
致 謝
序 言
王邦維
陳明又要出一本書,書名是《梵漢本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詞語研究》。他把書稿發給我,希望我爲他的書寫幾句話。這些年來,陳明很努力,研究中取得不少成果,成績突出,出版的書也有好幾種。其中最早的三種,我也寫過序, 現在還讓我寫序,好多話我已經説過,陳明也早已經成爲一位成熟的學者,他在他研究的一些領域内,甚至可以説小有名氣,我還能寫些什麽呢? 我因此有些猶豫。
不過,思量一陣之後,我還是答應了陳明,原因之一,是有關根本説一切有部以及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以及義净的研究,無論是書,還是文章,我一直有興趣,也一直很注意。而且這也讓我想到更多一些學術上的問題。
最早知道“根本説一切有部律”這個名字,已經是快四十年前的事。1979年秋,我到北京大學,跟季羨林先生念研究生。作爲季先生的學生,很自然的一件事,是找來先生的著作,不管讀得懂還是讀不懂,先讀一遍,有的還得讀不止一遍。季先生的書,當時能找到的,有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印文化關係論叢》,書中收有季先生1950年寫的一篇文章《記“根本説一切有部律”梵本原本的發現》。讀過這篇文章,我知道了三件事:第一、古代印度的佛教分派 别,稱作“部派”,其中一派叫“根本説一切有部”;第二、佛經包括經、律、論三個部分,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律,其中包括“根本説一切有部律”,三十年代,在今天的巴控克什米爾的吉爾吉特,一個牧牛的孩子在一座古塔裏發現許多梵文的佛教經卷,其中有一部分是“根本説一切有部律”;第三、“根本説一切有部律”,中國古代有漢譯本,翻譯的人,是唐代的義净法師。
我是初學,剛入門,季先生的文章,讓我長了不少的新的知識。我没想到, 我後來的經歷,真就跟“根本説一切有部律”以及義净有了更多的關係。那就是我從1979年到1982年,在季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我的碩士論文以及1983到1987年期間完成的博士論文。兩篇論文,後來都在中華書局出 版了,出版時的書名,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另一部是《南海寄歸内法傳校注》。這都是義净的著作,我的工作,是對義净的原書做全面的整理和校勘,加上詳細的注釋,再加上撰寫一篇研究性的前言。前言的篇幅不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的一篇,大約2萬字,《南海寄歸内法傳校注》的一篇,則有將近20萬字。
義净是中國歷史上到過印度,最後成功回來,同時還留下著作的最著名的三位求法僧之一(另兩位是法顯和玄奘)。義净一生,求法與譯經,成就都很大,其中最突出的,是把當時印度佛教最有影響,也最流行的戒律“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帶回中國,并且翻譯了出來。今天研究印度佛教的歷史和文獻,尤其是律部的文獻,離不開義净的漢譯,也離不開義净在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内法傳》書中提供的豐富的信息。
對於佛教史的研究而言,部派是一個討論了將近一百年的老問題。所謂“部派”究竟指的是什麽? 學者之間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説法固然有多種,但在我看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佛教最初分裂爲部派,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爲律方面的問題。這一點,我在《南海寄歸内法傳校注》的“前言”裏做過詳細的討論。與此相關的,是佛教文獻,尤其是其中的律典。一個很明確的事實是,佛教文獻的傳承,歷史上有多個體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部派。義净講到的“根本説一切有部”,雖然名字出現得比較晚,但却曾經是印度佛教最主要,也最有影響的部派之一。根本説一切有部的文獻,對於瞭解佛教文獻發展的歷史,也有很重要的意義。
至於義净翻譯的“根本説一切有部律”,我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一書的“校注前言”裏把它們做過一個簡單的列舉,列舉之後,補充了一句話,“它們中有的梵文原本已在近代被發現,因此譯本和原本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這是我三十多年前的看法,其實當時還該補充的一點是,藏文《甘珠爾》中的律典,也屬於根本説一切有部。漢地傳承的佛教戒律,曾經有過多種。西藏則不一樣,傳承的完全是根本説一切有部的律。而且藏譯的根本説一切有部的律,内容上還更全,更完整。
因此,對於中國學者而言,可以做的,首先就有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梵本與漢本的對比研究,還有是梵本與藏本,同時再加上漢本的對比研究。上面提到的季羨林先生的文章,雖然不長,討論的問題範圍也不大,但爲此開了先河。
這樣的工作,我多年前就想嘗試做一點。1996年,應重慶出版社的約請, 我把自己有關義净的文章集合在一起,編成一本書,書名《唐高僧義净生平及其著作論考》。在書的“前言”裏,我提到“書中本來應該至少有一兩個章節專門討論他的翻譯工作”。可是時日易得,轉瞬二十多年過去了,當年雖然有這樣的設想,但至今也没有着手。原因固然可以找出一些,但最大的原因,還是自己不努力。不過現在好了,陳明現在所做的工作和出版的這部書,正好就在這個題目的範圍之内,而且陳明的研究確實也做得很好。這讓我很高興。
讓我高興的還不止如此,我們的另一位研究生,博士論文的題目,是研究在西藏發現的一部梵文經典《律經》。《律經》的作者是德光。從傳承上講,《律經》就屬於根本説一切有部,是一部解釋和發揮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學理論的著作。瞭解印度佛教同時也瞭解西藏佛教的人都知道,《律經》不僅在公元七世紀時的印度很有影響,以至於義净介紹印度佛教的大師們時專門説了一句“德光乃再弘律藏”,傳到西藏以後,對西藏佛教戒律的理論與實踐也同樣有過重要的影響。這位研究生,十年前畢業,但他一直還在繼續他這方面的研究,不僅在西藏發現了《律經》的一個以前不爲人知的梵本,還在已知的藏譯之外,發現其他的藏譯。
類似的研究,中國的學者過去少有發言的機會,但現在的情况則有了很大的改變,我們不僅可以做這類很專門的研究,而且能够做得與國際上高水平的學者一樣的好,甚至更好。這當然讓人覺得高興。這方面的研究,每一項成果,只要做得好,都會增加我們對佛教文獻及其發展歷史的瞭解。
説到中國學者在相關研究上可以着力之處,與義净漢譯的佛經有關,我又想到上個世紀德國的一位學者JohannesNobel(1887-1960)。他整理出版的梵藏漢對照的《金光明經》的校勘本,其中的漢譯部分,使用的就是義净的譯本。JohannesNobel與中國的 陳寅恪先生相識,當年都是德國學者Heinrich Lüders的學生。JohannesNobel的研究,有些地方還曾經得到陳先生的幫助。陳先生後來在中國發表的文章,也不止一次地提到義净翻譯的《金光明經》。在他們看來,義净的漢譯,是研究的重要材料。陳明現在的工作,對照梵本,討論義净漢譯的“根本説一切有部律”中詞語,從大方向講,也可以説是繼承了這些學術前輩們開創的研究傳統。
總之,關於義净和義净的著作,包括他漢譯的各類佛經,以及佛教的根本説一切有部,有許多問題有待研究。歐洲和日本的學者早做過一些。大半個世紀前,陳寅恪先生有所注意。六十多年前,季先生在中國開了個頭。與過去比,今天各方面的條件,無論是研究資料,檢索手段,學術信息的交流,更好了許多,我們真應該利用這些條件,做更多的事。以今天中國的情况看,學者,尤其是年輕的學者們,只要認真,一定會做出好的成績。陳明就是一個例子。
最後,説一句話,祝賀陳明的這本新書的出版。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他還會有更多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13日
王邦維
陳明又要出一本書,書名是《梵漢本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詞語研究》。他把書稿發給我,希望我爲他的書寫幾句話。這些年來,陳明很努力,研究中取得不少成果,成績突出,出版的書也有好幾種。其中最早的三種,我也寫過序, 現在還讓我寫序,好多話我已經説過,陳明也早已經成爲一位成熟的學者,他在他研究的一些領域内,甚至可以説小有名氣,我還能寫些什麽呢? 我因此有些猶豫。
不過,思量一陣之後,我還是答應了陳明,原因之一,是有關根本説一切有部以及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典以及義净的研究,無論是書,還是文章,我一直有興趣,也一直很注意。而且這也讓我想到更多一些學術上的問題。
最早知道“根本説一切有部律”這個名字,已經是快四十年前的事。1979年秋,我到北京大學,跟季羨林先生念研究生。作爲季先生的學生,很自然的一件事,是找來先生的著作,不管讀得懂還是讀不懂,先讀一遍,有的還得讀不止一遍。季先生的書,當時能找到的,有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印文化關係論叢》,書中收有季先生1950年寫的一篇文章《記“根本説一切有部律”梵本原本的發現》。讀過這篇文章,我知道了三件事:第一、古代印度的佛教分派 别,稱作“部派”,其中一派叫“根本説一切有部”;第二、佛經包括經、律、論三個部分,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律,其中包括“根本説一切有部律”,三十年代,在今天的巴控克什米爾的吉爾吉特,一個牧牛的孩子在一座古塔裏發現許多梵文的佛教經卷,其中有一部分是“根本説一切有部律”;第三、“根本説一切有部律”,中國古代有漢譯本,翻譯的人,是唐代的義净法師。
我是初學,剛入門,季先生的文章,讓我長了不少的新的知識。我没想到, 我後來的經歷,真就跟“根本説一切有部律”以及義净有了更多的關係。那就是我從1979年到1982年,在季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我的碩士論文以及1983到1987年期間完成的博士論文。兩篇論文,後來都在中華書局出 版了,出版時的書名,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另一部是《南海寄歸内法傳校注》。這都是義净的著作,我的工作,是對義净的原書做全面的整理和校勘,加上詳細的注釋,再加上撰寫一篇研究性的前言。前言的篇幅不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的一篇,大約2萬字,《南海寄歸内法傳校注》的一篇,則有將近20萬字。
義净是中國歷史上到過印度,最後成功回來,同時還留下著作的最著名的三位求法僧之一(另兩位是法顯和玄奘)。義净一生,求法與譯經,成就都很大,其中最突出的,是把當時印度佛教最有影響,也最流行的戒律“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帶回中國,并且翻譯了出來。今天研究印度佛教的歷史和文獻,尤其是律部的文獻,離不開義净的漢譯,也離不開義净在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内法傳》書中提供的豐富的信息。
對於佛教史的研究而言,部派是一個討論了將近一百年的老問題。所謂“部派”究竟指的是什麽? 學者之間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説法固然有多種,但在我看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佛教最初分裂爲部派,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爲律方面的問題。這一點,我在《南海寄歸内法傳校注》的“前言”裏做過詳細的討論。與此相關的,是佛教文獻,尤其是其中的律典。一個很明確的事實是,佛教文獻的傳承,歷史上有多個體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部派。義净講到的“根本説一切有部”,雖然名字出現得比較晚,但却曾經是印度佛教最主要,也最有影響的部派之一。根本説一切有部的文獻,對於瞭解佛教文獻發展的歷史,也有很重要的意義。
至於義净翻譯的“根本説一切有部律”,我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一書的“校注前言”裏把它們做過一個簡單的列舉,列舉之後,補充了一句話,“它們中有的梵文原本已在近代被發現,因此譯本和原本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這是我三十多年前的看法,其實當時還該補充的一點是,藏文《甘珠爾》中的律典,也屬於根本説一切有部。漢地傳承的佛教戒律,曾經有過多種。西藏則不一樣,傳承的完全是根本説一切有部的律。而且藏譯的根本説一切有部的律,内容上還更全,更完整。
因此,對於中國學者而言,可以做的,首先就有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梵本與漢本的對比研究,還有是梵本與藏本,同時再加上漢本的對比研究。上面提到的季羨林先生的文章,雖然不長,討論的問題範圍也不大,但爲此開了先河。
這樣的工作,我多年前就想嘗試做一點。1996年,應重慶出版社的約請, 我把自己有關義净的文章集合在一起,編成一本書,書名《唐高僧義净生平及其著作論考》。在書的“前言”裏,我提到“書中本來應該至少有一兩個章節專門討論他的翻譯工作”。可是時日易得,轉瞬二十多年過去了,當年雖然有這樣的設想,但至今也没有着手。原因固然可以找出一些,但最大的原因,還是自己不努力。不過現在好了,陳明現在所做的工作和出版的這部書,正好就在這個題目的範圍之内,而且陳明的研究確實也做得很好。這讓我很高興。
讓我高興的還不止如此,我們的另一位研究生,博士論文的題目,是研究在西藏發現的一部梵文經典《律經》。《律經》的作者是德光。從傳承上講,《律經》就屬於根本説一切有部,是一部解釋和發揮根本説一切有部律學理論的著作。瞭解印度佛教同時也瞭解西藏佛教的人都知道,《律經》不僅在公元七世紀時的印度很有影響,以至於義净介紹印度佛教的大師們時專門説了一句“德光乃再弘律藏”,傳到西藏以後,對西藏佛教戒律的理論與實踐也同樣有過重要的影響。這位研究生,十年前畢業,但他一直還在繼續他這方面的研究,不僅在西藏發現了《律經》的一個以前不爲人知的梵本,還在已知的藏譯之外,發現其他的藏譯。
類似的研究,中國的學者過去少有發言的機會,但現在的情况則有了很大的改變,我們不僅可以做這類很專門的研究,而且能够做得與國際上高水平的學者一樣的好,甚至更好。這當然讓人覺得高興。這方面的研究,每一項成果,只要做得好,都會增加我們對佛教文獻及其發展歷史的瞭解。
説到中國學者在相關研究上可以着力之處,與義净漢譯的佛經有關,我又想到上個世紀德國的一位學者JohannesNobel(1887-1960)。他整理出版的梵藏漢對照的《金光明經》的校勘本,其中的漢譯部分,使用的就是義净的譯本。JohannesNobel與中國的 陳寅恪先生相識,當年都是德國學者Heinrich Lüders的學生。JohannesNobel的研究,有些地方還曾經得到陳先生的幫助。陳先生後來在中國發表的文章,也不止一次地提到義净翻譯的《金光明經》。在他們看來,義净的漢譯,是研究的重要材料。陳明現在的工作,對照梵本,討論義净漢譯的“根本説一切有部律”中詞語,從大方向講,也可以説是繼承了這些學術前輩們開創的研究傳統。
總之,關於義净和義净的著作,包括他漢譯的各類佛經,以及佛教的根本説一切有部,有許多問題有待研究。歐洲和日本的學者早做過一些。大半個世紀前,陳寅恪先生有所注意。六十多年前,季先生在中國開了個頭。與過去比,今天各方面的條件,無論是研究資料,檢索手段,學術信息的交流,更好了許多,我們真應該利用這些條件,做更多的事。以今天中國的情况看,學者,尤其是年輕的學者們,只要認真,一定會做出好的成績。陳明就是一個例子。
最後,説一句話,祝賀陳明的這本新書的出版。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他還會有更多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13日
本书以中古汉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系列律事以及其他律典为研究对象;以梵汉本《破僧事》《药事》《皮革事》、《摩诃僧祇律·明威仪法》、《出家事》等律典为重点,进行汉语史意义上的分析。本书稿利用已刊的梵语律典,与汉译律典进行比较研究,运用语言接触理论,不仅解释疑难词语的含义,而且梳理常用词语的演变历程,以揭示律典在中古汉语史研究方面的独特价值,对目前中古汉语史研究提供梵汉对勘的实证语料以及词语的解读,为探索中古汉语的词汇与语法演变的规律提供实证分析。
陈明,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印度古代语言文学 、佛经语言与文献、中印文化交流史(侧重医学文化交流史)等。著有专著《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等。
本书以中古汉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系列律事以及其他律典为研究对象;以梵汉本《破僧事》《药事》《皮革事》、《摩诃僧祇律·明威仪法》、《出家事》等律典为重点,进行汉语史意义上的分析。本书稿利用已刊的梵语律典,与汉译律典进行比较研究,运用语言接触理论,不仅解释疑难词语的含义,而且梳理常用词语的演变历程,以揭示律典在中古汉语史研究方面的独特价值,对目前中古汉语史研究提供梵汉对勘的实证语料以及词语的解读,为探索中古汉语的词汇与语法演变的规律提供实证分析。
版权所有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音像出版社
京ICP备09072562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4978号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新出发京批字第版0160